扬搜 | 广告 |
|---|
| 首页 | 财经 | 视频 | 图片 | 今日半价 |
|---|
| 百度热点 | 微博热点 | 天气预报 | 万年日历 | 扬搜精选 |
扬搜 | 广告 |
|---|
| 首页 | 财经 | 视频 | 图片 | 今日半价 |
|---|
| 百度热点 | 微博热点 | 天气预报 | 万年日历 | 扬搜精选 |
| 连载|我在故宫看大门[14/23] 原创:维一 日期:2019-05-06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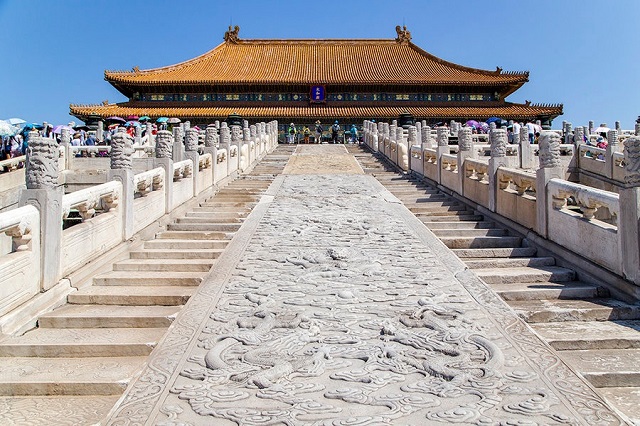 前后“点绛唇” 三叔是个戏迷。 三叔是我家在北京居住时的房东三老爷子家的小儿子,上过大学,在族里大排行老三,做小辈的都管他叫三叔。我是他们家的街坊,于是也就随了众人叫他三叔。 三老爷子早先在西单牌楼路南东边把口的地方开过一家西药房。那个年头懂西药的人并不多,懂洋码子的就更少,三爷把三叔送去读药学,为的就是家里的买卖日后能有个人照应。可三叔觉着“盘尼西林”、“可地松”这些东西忒没劲,经常逃学去药房间壁的长安戏院听戏。 从打长安戏院的那块地皮上还是“日升杠房”仓库的时候,三爷家的产业就已经在那儿了。日升杠房原先给西太后和孙大总统办过大出殡,八八六十四人抬的大杠着实火过一阵。后来入了民国,这类生意越来越不济,约莫到抗日的时候就歇了业,将这处库房卖给杨家开戏院。三叔说到这些总还有点得意,说“长安”当年为了省钱,开的还是吞头门,缩进街里头,不像三爷他们家的西药房可一直都是开在街面上。后来三爷家不开药房了,北京也解放了,长安和西药房都入了公,但三叔和长安原来的东家伙计交情倒是一直没断。 三叔小时候一直在长安听“蹭戏”,金少山、梅兰芳、谭富英这些人的戏没少让他占便宜。三叔人倒是老实,总是站在柱子前头不说不动,挡不住别的观众,别人叫好,他也不言语。三叔后来告诉我说,你们南方人不懂,过去北京人到戏园子里去不说“看戏”,而是说“听戏”,这是因为北京的旧戏园子原是脱胎于茶楼,前台的观众席上,茶桌的摆放与舞台垂直,茶桌两旁的观众脸对脸地对面喝茶,耳朵却向着舞台,非要到了精彩要紧之处,观众才会转过头去完整地看演员的做派。三叔说,长安要是这路戏园子,就像前门外的“广和”或者“天乐”,加上他又认识那么多长安的伙计,满可以大大方方地坐着听戏。可长安改革了,不兴桌椅板凳和茶壶茶碗,都是排座,虽说那时候还是条凳,不是后来的一人一座,但夹在哪儿别人都不乐意,要是看见个空座就坐上去,来了人你总得让开,所以还是站在柱子前头“贴对联”听戏自在。 三叔上了中学就不听“蹭戏”了,一来在长安认识的老人越来越少,二来三叔说,熟人都知道他是原先隔壁西药房的少东家,听“蹭戏”显得忒寒碜。三老爷子缠不过他,就给他两个闲钱去买票,笑着说:孩子大了,也知道害臊了。 后来三叔又去上了大学。虽然读的是药学,但三叔的兴趣本不在此,所以除了本科之外,总是去旁听历史和国文,而且不管哪个大学都去,坐下就听。他最喜欢的是北大孟心史先生的明清史,说老先生为人厚朴,学问精深。班上的学生也都说,孟先生可能不知道现在街上的萝卜白菜多少钱一斤,可成化年间或者雍正年间当街谁给谁一个嘴巴他可知道得真真的。还有就是燕京大学的邓之诚先生,他的课三叔也爱听,说是听了邓先生的课才知道学问里五方四部触类旁通得要紧。 三叔说,他听这些课其实都是为了钻研京戏。京戏博大精深,不懂历史文化,听戏听的是热闹,只有胸中有了涵养才能听出门道。他常去阜成门里和西四的那几处尚存一息的票友集会点,他说没有赶上当初京戏风光的好时候,如今有点凤毛麟角就得抓紧了。他到那里去,为的是以戏会友,汲取些亲身体会。起先他并不唱,只是听,有的时候在关节处还能讲上两句要紧的话,所以戏迷们都称赞三叔是个有学问的人。 我初见到三叔的时候已是五十年代,三叔那时候虽然还年轻,但已经上完大学,还没有找到事由,正赋闲在家里。三叔经常穿着一身蓝咔叽布的学生装,式样绝对不同于当时赶时髦的列宁装或者中山装,那是直领、挖兜,做工也讲究,左上兜里永远插着两三管钢笔,头发也是梳理得一丝不乱,看起来十分的精神。 三叔有了这份仪表,扮相自然就好。后来戏迷们一撺掇,三叔还真票上了。原先去的是老生,有时也反串青衣。不过嗓子不亮,他自己也知道,所以一来二去,三叔就学上场面的活儿,不但京胡、弦子都好,如果司鼓,场上的板眼也控制得得当。因为三叔肚子里会的戏特别多,一招一式又早都烂熟于心,所以戏迷们都要三叔掌场面,说要是彩演,出了上场门,一过九龙口就交给三叔,心里特别踏实。 后来经三叔介绍,院子里搬来一家正经在剧团里唱戏的梁先生夫妇。梁先生两口子原先都是在中华艺校坐科学的艺,梁先生在行里排的是“金”字辈,学的是老生,后来曾经红极一时的王金璐、袁金凯等人和梁先生都是同科的师兄弟。梁太木唱的是花旦,唱功尤其好。梁家租的是北屋西头的耳房。每逢周末,剧团的同事演了一个礼拜的戏还嫌不过瘾,周末还轮番到各家去凑戏。有时候就会凑到梁家来。我们邻居也乐得白听“蹭戏”,早早地就把葡萄架下的空场拾掇干净,茶水预备妥帖。 一般的时候,梁先生夫妇早在来人之前已经冲着院墙吊了两三回嗓子,所以文武场面一支好就可以开戏。因为地方窄,所以身段都不大带出来。选的段子又大都着意在唱功上,梁先生擅长的是袍带老生,梁太太爱唱闺门旦的戏,剧团里来的人都说梁家夫妇就像是戏文里唱的那样:琴瑟合鸣。听这么一说,连我们做街坊的都觉得与有荣焉。 三叔原本就懂戏,自从梁先生夫妇搬到我们院子里之后,又搭上自己有的是闲工夫,就愈发朝京戏上靠过来。三叔起得早,梁先生夫妇头天晚上一般都有演出,起得晚。三叔怕吵了他们的觉,所以早上都是研究戏文,过了晌午,梁先生夫妇起身以后,或是出门上剧场之前,三叔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讨教。三叔到底受过高等教育,知识上总不吃亏,所以三叔对于戏文上的一些了解,梁先生有时候都说不上来。 三叔虽然只是业余票戏的戏迷,可是并不浅尝辄止,时常还爱个钻研和改进。凡是他看到不足的地方,总要提出建议。有的时候梁先生把三叔的意见捎回团里去,团里还真采纳。 譬如说,三叔对念白很讲究,说是“千斤念白四两唱”。有回梁先生念了一段《乌龙院》里的韵白,三叔听了说,你把该入“梭拨辙”的入了“怀来辙”,听着不熨帖。梁先生还把原先“姑苏辙”的一段引子改成“一七”和“姑苏”两辙混用,三叔说这要是小花脸念京白还凑合,可老生的韵白就显着别扭。梁先生说这还是团里指导特别纠正的。三叔说,皮黄的道白是有些乱,例如古音里“灰堆”与“一七”这两韵并不分开,但“十三道辙”里绝对不能混用,古音“中东”和“庚青”两韵严格不同,可中原音韵里早已一致。后来三叔和剧团的指导还仔细讨论了一回,指导说,没想到三叔对皮黄的音韵还真有研究。 还有一回梁先生夫妇在吉祥戏院演《武家坡》,请三叔去看。回来之后,梁先生问三叔的意见。三叔也就直说。他说在院子里听见你们两口子唱过好几回,没有身段和动作,不觉得什么。到了剧场有的地方就觉得不是滋味。比如说“跑坡”这一段,梁先生去的薛平贵一个劲儿地唱,梁太太您的王宝钏坐在那儿跟没事儿人似的,这感情就不对。多年没见到丈夫了,怎么能那样?您两口子天天见面还厮抬厮敬的,好得跟一个人儿似的呢,更甭提人家薛平贵和王宝钏了。不管是怨、是喜,您总得有个身段,给个眉眼不是?尤其是您梁太太的眼神特别有戏,在旁边给梁先生这么一配,那彩儿就全出来了。三叔说,其实这样类似的话齐如山老先生早先跟梅先生就说过。这一出戏,非得红花绿叶相互扶持才能交相辉映。 直到今天,我走在波士顿的街头上,一不留神哼起《武家坡》里薛平贵的西皮导板“一马离了西凉界”,就不禁想起当年的三叔和梁家夫妇。 这样快活的日子没有两天,外边的形势就越来越紧。三叔是个不懂世事的人,但眉眼高低也还看得出来,他这么老大的一个人,还上过大学,总闲在家里住着太招眼,也不是个说法,于是就托人在铁路局谋了个差事。因为他学过药,领导以为他肯定懂医,想派他到铁路医院给人瞧病。三叔连说那可不行,医学和药学大不一样。领导也闹不明白其中到底有什么不同,既然三叔一定不肯去,必是有他自己的难处。后来领导就派了三叔在丰台那边管药品采购。三叔受的是大学教育,管这点事可说是游刃有余。后来领导听说他还会唱戏,就让他兼管工会,负责组织晚会和跳舞之类的事。三叔说,这不像给人瞧病,绝对出不了人命,倒还可以。 三叔管工会挺上心,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,前门火车站改成铁道俱乐部以后他就成天往那儿跑。领导看着三叔的工作有成绩,别的兄弟单位都夸奖,脸上有光,心里也高兴。有时候三叔也请梁先生去指导一番,除去原本的几出折子戏之外,还排了《法门寺》、《凤还巢》那样各行齐全的整本戏。日久天长,三叔和梁先生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,整天在一起切磋技艺。 没想到的是,到了一九五七年,唱了一辈子京戏的梁先生,让人给揭发出来政治问题了。说梁先生藐视领导外行,而且在帮助铁路工人排戏的时候,还用旧社会名牌演员的生活排场来腐蚀工人老大哥。因为梁先生是三叔介绍来的,所以就追问他和三叔的关系,在一块儿还说过些什么。梁先生是个讲义气的汉子,于是就来个装傻充愣,没咬三叔一句,让三叔总算躲过了一劫。结果梁先生不久就被打成了“右派”,好在上面念梁先生原本也是苦出身,说的话也不算太出格,就没有送去劳改,罚他到陕西的剧团去唱配角儿,梁太太带了孩子也跟了去,一家人就这么都走了。三叔原本要到车站送梁先生,梁先生说,这可别介,正说咱们俩勾连搭呢,你再送我,不是尽等着把你给提溜出来,我也罪加一等么。三叔寻思梁先生的话也对,想到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于是就作罢了。梁先生获了罪,可嘴上还不软,他对三叔说,早年间要是戏班得罪了地面上的官家,都是由“经励科”报官的领班去受枷锁,不能连累他人。如今我就是那“经励科”的,我不怕见官。 事后三叔在院子里看见北屋耳房里原本梁家的房子搬得空空如也,不免长叹了一口气,恨恨地说:“都说‘婊子无情,戏子无义’,可我看人家梁先生可真是有情有义。天大的事一个人扛着,宁可自己吃亏,也绝不把我往里边拽。倒是有那兔崽子,连婊子都不如!”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三叔这样发怒,可见他心里是真动了肝火。 从那以后,三叔在单位里就再也没有一句实话。三叔私下对我说,原先以为干工会不像当大夫,出不了什么人命,谁知道这回半条人命也快搭进去了,工会干事横竖是说什么都不干了。领导问起来,他的理由是家里负担太重,身体也不行。领导听了明知三叔有情绪,但也拿三叔没办法。 三叔原本混在梁先生那儿,不觉着怎么,现在梁先生一走,三叔一下子就像变了个人,每天痴呆呆的。大伯是三叔的哥哥,他怕三叔总是这样会闹出毛病,就提议让三叔没事的时候教他孙女小婉唱京戏。小婉那孩子,别瞧才几岁,但人机灵,跟三叔学过几回,唱得就有模有样了。三叔看着也高兴,说这京戏百年不衰,靠的就是一代一代的后继有人,无论是演员、票友还是戏迷和观众。 后来三叔又对京戏曲牌上了心思,那时候北京市图书馆就在头发胡同西口,听说那里收藏的唱本俗曲挺多,三叔经常去翻翻,算是把心思多少稳定下来了。 记得有一回,我听见收音机里放京戏,升帐的音乐挺好听,就问三叔这是什么曲牌。三叔听了之后说,这是《点绛唇》。 我不懂什么是《点绛唇》。三叔就说,《点绛唇》又叫《点樱桃》。大家形容美人的时候不是总说“柳叶眉,杏核眼,樱桃小嘴一点点”么,点樱桃就是画嘴唇,原本是个好艳的说辞,谁知后来一来二去的成了雄壮威武的牌子了,在起霸、升帐或者出兵这样的场合都用在里头。 三叔又说,说起《点绛唇》,现在看来“樱桃小嘴一点点”不见得有多好看,中国人的审美观也变化了。但是要学外人,总不能过分,得按照咱们自己的特点改。“就说这京戏吧,”三叔的话绕来绕去又回到京戏,“就像这樱桃小嘴,要是愣跟洋人似的咧开有半尺长的大嘴叉子,”说着,三叔还用两手的小拇指钩起两个嘴角往外一抻,道:“放在咱中国人的脸上,你说他能好看得了吗?” 三叔见我听得人神,更来了兴致,跟我说,其实还有一段曲牌叫《粉蝶引》,比《点绛唇》气势还大,都用在《霸王别姬》、《挑滑车》这些戏里。三叔又说起好些曲牌,像《水龙吟》、《柳摇金》,现在都没了唱词,在京戏里光作音乐用。 后来三叔又谈到京戏的布景,说胡适之先生当初就不以为然,认为京戏跳过桌子便是跳墙,站在桌上就是登山,四个龙套就是千军万马,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,真是荒唐得可以!说到这里三叔笑了一笑,说这就是胡先生不懂中国东西的地方了。就像中国国画的大写意,意在似像非像之间,中国人讲究的是行云流水,这种抽象的审美观非深入进去是很难理解的。胡先生虽是大学问家,但就这件事的见解,他不如说相声的侯宝林。侯先生的段子《戏剧杂谈》比胡先生对京戏的理解高明许多。你看直到现在,凡是往舞台上胡乱加布景道具的,没有一个成功的。 那天只是因为一曲《点绛唇》,引出来三叔一大堆关于京戏的说教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,大约是形象的比喻吧,三叔在那个下午的一席话,如今我只记住了他的《点绛唇》,并且还认为,三叔对于京戏的理念都在《点绛唇》的解释中得以体现。多少年之后,听说三叔还专门写过一篇讲南北昆腔源流的文章,里面还特意以《点绛唇》为例详加诠释,但那已经是过了几十年的后话了。 自从三叔成了家,搬到丰台去另立门户单过之后,我就很难见到他了。只有途年过节,或是有的礼拜天三叔来瞧三老爷子的时候,我才能和他照个面,但也难得说上两句话。不过如果有话说,三叔的话题必定是离不开京戏。他还跟我开玩笑说,你总喜欢那套洋的,其实也得掺和一点土的。我敢说,你会有一天想起京戏来,可又听不着,浑身上下都不自在。后来过了好些年,我到了海外,这才体会出三叔的意思。 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大概是三老爷子托人捎信嘱咐了,所以三叔就很少到我们院子里来。加上我们家也出了事,谁还有心思打听三叔呢。倒是二爷家的二妈有次说走了嘴,说三叔也出事了。全院子的人都想不通,说三叔不能说是生在红旗下,但差不多应该算是长在红旗下了。原先就是个学生,什么党派都没有参加过,最大就当过两天工会干事,可他上头还有工会主席呢,即使犯错误也轮不着三叔哇。 不久还是三爷家透出口风大家才知道,原来三叔有个同学爱唱京戏,和三叔很要好,后来去了美国,一直就和三叔通信往来,有的时候还给三叔寄回一些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和票戏的剧照。 那个同学在国外学的是西洋戏剧,三叔经常和他通信讨论。那个同学文思敏捷,眼界又广大,笔头上也健,评论京戏表演的得失,特别是和西洋戏剧进行对比研究,说得有条不紊、头头是道。三叔很珍惜这位朋友的信件,都一封封贴在本子上,有时拿出来翻翻,温故知新,总有新的心得体会。 解放没几年,三叔和那个同学之间也就断了音信。三叔的这些信件都塞在柜子里头,多少年也没动过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,红卫兵抄三老爷子的家,变天账没有找出一本来,可三叔的这些信件给翻出来了,有的上面都是外文,另外还有那个同学在国外毕业时候戴博士帽的照片。红它兵以为那是个教堂里的神父,说这回可逮着个与外国有联系的大坏蛋,而且还信洋教。这样一来,三叔这么个最远只到过河北保定的人,没想到给安上了个“里通外国”的罪名。 从那以后,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三叔的消息,就像三叔喜欢了一辈子的京戏那样,从我的生活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 日子一晃就是三十年。上次我从美国回到京城,特意去原来住过的院子瞧了一眼,还真见到了三叔的侄子。听他侄子说,三叔现在早已退休了。别人劝他说,既然身子骨还行,其实可以再干干。三叔笑笑说,我要是有劲也还得留点儿干我爱干的事儿呢。虽说三叔不上班了,可是据说比上班还忙。除了几个票戏圈子里的文武场上缺不了三叔,单是三叔说戏,特别是自打五十年代初就成绝响了的那些老戏,就够老爷子忙活的。像《别母乱箭》、《英烈奇缘》,好些梨园世家的子弟都说不上来,都得听三叔的。三叔还经常到潘家园各处搜集旧戏本儿和旧戏单子,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大堆关于京戏流派和历史的文章。他侄子说,三叔有时候还念叨起我来,说那是个洋派儿的人,可对京戏还能接受,其实靠的全是他的提调。 我一听说,连忙就打听了三叔的住处,到底抽了个空去看了一趟三叔。 三叔看来老多了。一想也是,三十多年没见面了,就是天天过舒坦日子的人也经不起岁月,何况让人曾经这么来回折腾的主儿。当年三叔是在胡同里看着我长大的,这回一见我,还能认得出来。寒暄之后,我就说起想和三叔扯扯老事儿,特别是听说他近年来搜集了不少的旧戏文和老戏单。 三叔一听就来了精神,大笑道:“虽说你到了美国,可看来这瓤子里头还真是没变。” 我长叹了口气:“唉,要变也难。您不知道,在海外只要一听见大锣那么一敲,京胡那么一响,我那眼泪哗啦啦的就往下掉哇!” 三叔点头称是,得意地大声道:“怎么样,原先我怎么跟你说的来着?” “可是我听说,这京戏在京城反倒不景气啦?”我接着问三叔。三叔不言语,微微侧过头去,随便打开一份夹子,从里面小心翼翼地抽出一张老戏单,对我说:“人家说我是研究京戏,其实眼下我这是在戏单上琢磨京戏的发展环境。你看,这是当年杨小楼老板在吉祥唱戏的戏单,票价是五毛。我翻了翻资料,那时候一个中学教员每月总得关个五十块。可现在的长安,最便宜票价也得六十块,最贵的敢要你八百,还甭提你有没有杨老板的那块料。老说京戏没人看了,可你不说,就这票价不把戏迷全都给杀没了么。这戏好比是树,观众就好比种树的土。想把树种好了,那先得把土给侍候好了。‘戏靠戏捧,也靠人捧’,这是玄黄年间的老话儿了,用在现在,我瞧还对。” 提起长安戏院,三叔对我说:“我这儿正有几张赠票,就是今天下午,说是让我去给提提意见。你要愿意,咱们就一块堆儿去瞧瞧。” 我在美国就听说老长安给拆了,有这么个机会去看看新长安戏院也不错,于是满口答应。和三叔一起随便扒拉了两口三婶原本给三叔一个人预备的炸酱面,就随着三叔出了门。 新长安修得倒是讲究,但吃惊的是池座改成原先早年间茶园的阵势了。想当年,长安不说是头一家改成排座的,也得算是头几家。这回看来又带头往回改了。 大概是内部观摩,稀稀落落有个三成的座儿。开锣的戏是《三岔口》。去任堂惠和刘利华的两个武生在台上胡乱比画了一回就出了下场门,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,也不像是在夜里摸黑争斗,倒像是空手道。 接着是《白蛇传》,拆成几个折子演,台上的人糊弄了一阵,台下的人也就快睡着了。倒是演到“婚宴”一场,锣鼓大作,白娘子与许仙坐到台下观众席里,跷起腿和观众一起与民同乐。台上换了人,踩超高跷、耍上绣球。我偷眼看了一回三叔,三叔挑了挑眉毛,默不作声。 过了“水漫金山”一场,白蛇扣在雷峰塔下,突然从观众席后面响起一声哭喊,原来是许仙的儿子从观众入座的太平门外冲了进来,跑上舞台。我先是一惊,等我醒悟过来,觉得真有如当年上海来京汇演的魔术大师张慧冲的节目;大变活人。 这次还没等我侧过头去瞧三叔,三叔就扯着我的袖子一起出了戏院。 我看三叔低头不语,就对三叔说,这京戏是全北京城都这么改,还是长安一家这样?三叔好半天不说话,后来说,这是我不好,其实应该带你去平素和我一起票戏的那几家走走,那里还有些真东西可以看着。我原先是想,你在海外待的时候久了,没准儿喜欢这些海派的玩意儿。不过听你这么说,我又挺高兴,你居然还能惦记着正经的京戏。当然我不是说京戏不能改,而是说怎么改。一是不能长袍改马褂,马褂改背心,越改越没东西;二是不能大襟改西服,那横竖也改不了。你看,桌椅板凳、茶壶茶碗改成排座,我就举双手赞成。戏后鼓掌,演员谢幕也是好的。可是不明白怎么长安又要改回茶壶茶碗来了。而且现在讲究的是,不管戏唱到哪儿了,观众也不管懂是不懂,张口就大声叫好,这我就不赞成了。 听三叔这么一说,我也就班门弄斧,说了一回我的感想。我说,长安的排椅学的是洋人,其实西洋戏剧的种类截然分开,有歌剧、舞剧和话剧。他们的舞剧非看不可,歌剧和话剧则根本不讲究身段,走上两回台步已然算是很好的了。前些年我在德国拜伊罗特的剧院看瓦格纳的歌剧,台下的好些老戏迷都是闭着眼,手指头尖敲着一板三眼的节拍,其实也是在“听戏”。所以要说是“听”戏,西洋的歌剧倒是可以光听,可中国的京戏却非“看”不可。说看京戏,反倒是洋人的法子好,京戏讲究的是做、念、唱、打集于一身,如果只是“听戏”,那么一出戏下来只得“念、唱”,而失去“做、打”,兴味差了一半,实在可惜。 从长安出来,天色尚早,三叔说要不嫌弃,就再到他家里小坐,顺便可以看着他的戏单,他知道这些戏单我一直想要过过眼。可我想三叔陪了我一天,够累的,就推说晚上还有个朋友给我饯行,这回就不去了,下次再去拜访。三叔说这样也好,他收集的一大部分戏单正托琉璃厂那家的刘掌柜去裱,下次回来一定能瞧见。 我看三叔意犹未尽,就说虽然老长安全拆了,但我还想看看当年长安戏院的具体方位,要不介咱们先到长安旁边的庆丰包子铺吃几个包子,填填饥,您再给我比画比画? 三叔一听就笑了,说哪儿还有“庆丰”啊,连“天源”都拆了。 我先吃了一惊,连忙说:“那同春园呢?” “也没了,”三叔说,“看来你对现在的‘单牌楼’那一带可是真不熟了。这样吧,你也别客气,我也不破费,咱们爷儿俩打个车到西单,我请你随便吃点什么,到了长安那里,我给你略微指点一下,然后就分手。你看怎么样?” 我连说大好,只是又得偏劳您。三叔说这是哪儿的话,你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,咱们真该好好聊聊。不过话说回来,这事要是放在过去,说好听了,我这是陪同外宾呢,要是说得不好听,我这可就是里通外国。我知道三叔还是记着他在“文革”里的那档子事,不禁笑了。我们说着打趣的话,上了一辆出租车,一溜烟似的到了西单。 下了车,三叔买了两个汉堡包,递给我一个,说你们在国外见天就吃这些难吃的玩意儿吧?我说,也不介,不到万不得已我是绝对不吃。我们一边说着话,一边过马路,突然三叔停在马路当间儿不动了,对我说“这儿就是原来我们家的西药房”,又向前走了十几步,说“这儿是原来长安大戏院的正门口”。 看三叔那个聚精会神的样子,我怕他给街上的汽车碰着,连忙说:“老爷子,您留神,瞧着点儿。” 三叔根本不在意,又向前跨了好几步,旁若无人地说:“到这儿你就全知道了,这是你小时候,长安在大街上露出门脸儿的大门,那边就是休息室,再后边不就是后台了么?” 街上的汽车风驰电掣,我真怕三叔出个好歹,赶紧走过去搀他。 过了马路,我们站在便道上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。这个城市我几乎认不得了。见身旁卖报的小贩吆喝得热闹,我就顺手买了一张他的报纸,只见背版上是大幅的通栏广告“弘扬国粹,精彩京剧,声光电化,魔幻惊奇”。 我忽然想起刚刚瞧过的京戏,随口问了三叔一句:“您说这京戏会玩儿完么?”说完之后我又觉得有些唐突,我知道,京戏可是三叔的心尖子。 三叔倒是没有在意,似乎是早就用心想过这个问题。他打开折扇,还是沉吟了片刻,然后抬起头来认真地看着我说:“要是依我看,说白了,这京戏就像是一棵枝高叶茂的大树,非得有大的树根不能成活得下去。这树根……”说到这里他顿了一顿,接着说:“就是不但得有好戏园子,有好戏文,有好戏子,还得有好些懂行的戏迷。我是迷了一辈子的戏,而且从来不反对改革,过眼的玩意儿甭提有多少了。我看来看去,这京戏就像是这老北京城……”三叔说到这儿摇了摇头,咳嗽了好几声。 “怎么样?”我急切地要听他的下文。 三叔不知是嗓子咳嗽延着了时间,还是因为生出什么别的念头,突然转了口风道:“嗯,我看或许还有希望。” 我没有马上搭他的下茬,三叔待了好久才长叹一口气说:“我这是怕它亡啊!” 三叔这话像是对我说,也像是对他自己个儿说。 我怕三叔过分伤感,突然想起从小跟着三叔学过戏的小婉,于是连忙转了个话题问他:“对了,您的侄孙女小婉现在怎么样了,还学戏吗?” 听我说到这儿,三叔并不答话,只把下巴颏儿往前一努,推了推鼻子上的眼镜,然后带着意味深长的一丝微笑,侧头对我说道:“早不学了。你瞅见对面儿过来的这二位姑奶奶了么?现在人家喜欢的都是这个样儿。”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朝前一望,果然正有两位年轻女子出了长安街南侧的地下道,款款地往我们这边走来:只见上身的夏装薄如蝉翼,掩不住的半抹酥胸,头上顶着的遮阳伞下,面孔显得出奇的白嫩,肩上背着的正是“蔻齿”名牌皮包。要不是监回京城之前经人点拨,我还真不知道这类玩意儿在波士顿非得是高档商店里才有得卖呢。 等二位姑娘走到近前,我发现她们脸上原来是扑了厚厚的一层粉,远看像是细皮嫩肉,近看不留神细瞧还以为是勾了白脸的曹操,嘴唇上的口红涂得血紫,还特意往嘴角两边拉开了许多,好像是学着好莱坞当家花旦朱莉娅·罗伯茨的大嘴叉子。 等她们走过去,三叔把折扇收起,用扇子骨不停地击打着另一只手上大拇指的指甲盖儿,像是多少年前他在场面上用鼓箭子敲着单皮上的鼓点儿。敲罢,他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空,若有所思地俯在我的耳朵上说:“你们洋派儿的人不是总好说个‘后’现代,‘后’文化什么的吗?那我就给这路货色起个雅号。” 不等我言语,三叔狡黠地一笑,轻声地说:“我管这叫‘后点绛唇’。” 说话听声儿,锣鼓听音儿。我不知道三叔是光指眼前过去的这二位姑奶奶呢,还是也指我们刚才在长安听过的京戏。 来源:老衲说说 作者:维一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,转载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文章搜索: 维一 老衲说说 故宫 生活 |
文章平均每篇阅读排行: 一月丫头 149590 夏梦爱金庸 63205 王孟源 49203 夕月木 48036 Sir 45868 鱼人 45410 大头 41562 少年A 36801 任小酒 34521 喜乐阿 34021 董指导 33875 内幕君 22283 |
扬搜7天搜索词排行: 政事堂 央视网 20 顾子明 2019 焦点 政事堂2019 美国 中国 中美 韦居善 新闻联播 卢克文工作室 俄罗斯 起 经济 新闻 岱岱 全球 房地产 5g 江西 新时代 一棵青木 |
 | 原价: 39.90优惠价 查看或购买>>> 淘口令: 69¥jPpP2tp8anB¥ https://m.tb.cn/h.UZbvgwh CZ0001 淘口令 (复制,打开淘宝App) |